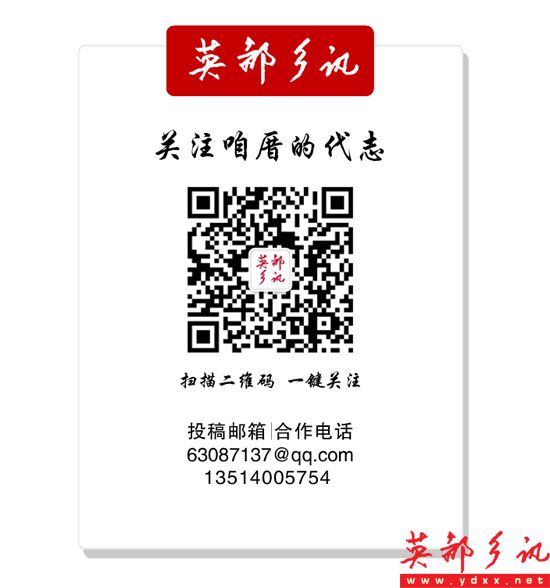图片来源于《泉州晚报》
我的奶奶生于20世纪初,是位缠足女子,虽半生糠菜,一世坎坷,但她总是迈着碎步,一双有神的眼睛闪烁着从容与自信。
关于奶奶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可以说,她的言行影响了我的一生。特别是奶奶的话,有些堪称“经典”,诸如“光光月不如小小火”“月儿再亮也晒不了谷子”“宁跟能者吵嘴,不与庸人说笑”“千元该花,一分得省”……你说,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奶奶说的话,像不像有学问的先生?
在记忆深处,奶奶的篾匠手艺最不该忘也忘不了,论技艺,她算得上业余中的专业。
奶奶身形匀称,清瘦如竹,虽有一双“小脚”,却有一双有力大手。也许正是这双生活练就的“糙掌”,使得她的生活技能几近满分。
屋后有片竹林,那年月的居家生活,竹制品防潮耐洗,寒暑通用,几乎占据生产生活用品的半壁江山。
箩筐、簸箕、鸡罩、鸭笼、兔栏,还有吊篮、火篮、摇篮等常用的竹制品,大多由农贸集市买来。“吊篮”悬于灶屋梁下,既防蟑螂老鼠,又透气散热,相当于现在的冰箱;火篮里瓷外竹,是冬天烤火用的;而摇篮是哄婴儿入眠的,从前有“一个摇篮传三代”之说。家里这一应俱全的竹编,大大小小,新旧交替。那些“超期服役”的,常有破、空、漏、透状况发生,旧东西舍不得扔,这时候奶奶的竹篾手艺便派上用场。别瞧奶奶的手掌粗大,十指却灵巧。一般小坑小洞的,对她来说简直不在话下。平常补个竹筐,只需几分钟。
稍懂竹篾手艺的人往往知道,破竹为篾是竹编的一道工序,既有“技术含量”又是力气活,这也是为什么民间篾匠几乎没有女性的缘故。况且这之后一系列过程的顶托拉拽,哪一项都少不了巧劲和韧劲。比如破竹时,需从竹尾起刀,如此才不至于溜偏。如果是四分之一开,中间需夹个十字架,再拿刀背匀力敲打。
小时候我问奶奶这手艺是哪里学来的,她笑说:“逼出来的本事,家里这么多破筐烂箩,扔了可惜,补补能用。”就是这简单朴素的初心,道出了竹的虚怀,篾的坚韧,成就了一个家庭女性的竹篾工匠手艺。
一件竹器旧了坏了,不固定破损哪里,总得要修。筐壁、篮底、笼角、箕口,或镂或密,或方或圆,奶奶总能根据旧物原样,既“修旧如旧”又重焕新颜。
听内行人说,竹制器皿,通常修旧不比新编容易,甚至更难。奶奶那双糙得开裂的大手,好似天生具有雕琢之功,经她修葺的旧品,纹理契合,松弛适当,质地美感跃然竹篾之间。
尤为可贵的是,因为“名声在外”,常有左邻右舍请奶奶帮忙,奶奶自然“当仁不让”,所以人缘极佳。奶奶的性格既实诚又谦虚,她说自己的篾匠手艺不是祖传更非专业,连锯子、刨子、凿子、斧子都没有,只有家用的镰刀、菜刀和剪刀。她的意思是,只要别人不嫌弃,就凑合对付吧。
母亲常对我们说,别人夸我针线活好,其实你们奶奶的竹篾手艺才是左右难寻。还真是的,奶奶的篾匠工艺,既“补”了自家又“贴”了邻家,真叫有“用武之地”。
过去的日子已远去,只是记忆何曾褪色。一根扁担挑两个箩筐,一头孩子另一头生活琐碎。须知扁担和箩筐皆源于竹篾,是自然界的慷慨馈赠,承载着人们的托付和希望。
奶奶用一双灵巧的茧手,传承着俭朴家风,编织着光阴故事,也诠释着她的匠心美德。
注:原文刊登于2025年9月15日《泉州晚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