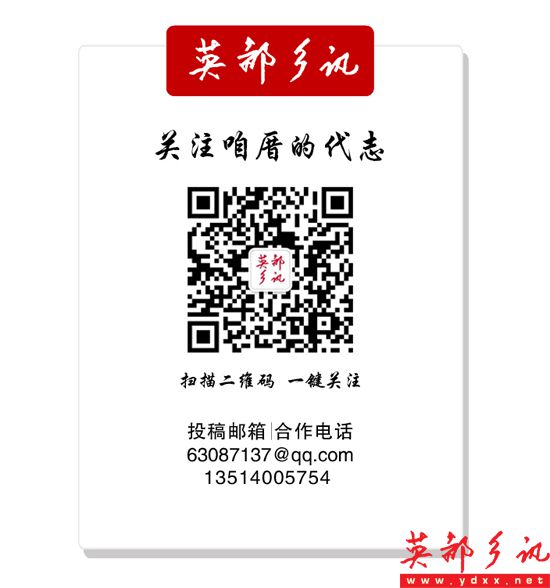我从小愚钝,或者说开窍较晚,反正我到9岁才上的小学一年级,现在的孩子这个年龄都快上高年级了。
大概10岁左右我还不会看钟表。奶奶让我到隔壁林先生家看几点了(那时候一座大厝就他家有口闹钟)好做晚饭,回来我用拇指和食指比划着说:“差这么多五点半”,一时间在整个生产队闹成笑话。
后来听学校老师跟我家大人说,这孩子只是上学晚点,“入戏”看似较慢,但整体还不笨。看这五官脸面,应该是个读书人的料,你们放心好了。
那时候一个班里的学生,年龄相差几岁是正常的。即便到了小学二、三年级,插班的留级的辍学的,走马灯似的。特殊年代贫穷底色,一切不足为奇,哪像如今规矩方圆,整齐划一。
人说“一朝先,吃遍天”,我从“起跑”就晚了一步,也许是这一步之遥,让我之后的人生列车经常赶不上趟,总是掐不到那个点上。然而我却觉得这其中有忧有喜,既然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肯定有其内在的道理。
小时候我总有点自卑或者腼腆,老觉得自己比别人笨,比如我打小不会玩扑克不会下象棋,更不懂麻将什么的,不是不玩,是怎么也学不会。
等到大一点,我终于学会一款单人玩法的扑克游戏,后来听人说那叫“接骨”,是扑克的最低级玩法。然而这时候我却不以为然,不就是玩吗,开心便好,哪来那么多讲究。直到现在,我于休闲时还会不自觉地玩它一把,不为别的,只为调节一下情绪。
渐渐地,关于“玩”我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也许是缘于自己从小天资偏弱,形成后来做事总是退而求其次,总是难登“高雅”而落入“低俗”。再后来索性我行我素,高兴便好。
童年时,如果找不到“称心”的伙伴,我便一个人玩泥巴造屋,建了拆,拆了再建,乐此不疲。别人喜欢抬头仰望大雁南飞,我却喜欢低头看蚂蚁迁徙,它们有推的有驮的,有单挑的有群力的,热闹非凡,我一蹲好几个小时,经常忘了吃饭和上学。

(图源:CFP)
也是秉性难移了,长大后我仍是大事干不了,小事则很执着。记得十几二十年前,铁树还是稀罕物,但我家楼顶种了许多。我经常挑土粪上楼顶,每天清晨必到顶层观察每棵铁树的生长情况,哪棵新开了几片叶子都心中有数。
有人说我“大器晚成”,我当然知道那是揶揄的意思,大器不敢说,晚成嘛,当然成熟得晚,虽有点惭愧但我必须承认。关于这一点,我有时候也耿耿于怀,这也能算缺点?
还好我一生有个嗜好,就是喜欢读书,这多少能弥补或掩饰自己身上一些缺憾。中年以后,偶然读到周国平的“世上有味之事……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再往后,当我知道一些重量级名人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们小时候的童真童趣时,还真为自己的“俗气”开脱不少。大人物尚且如此,况乎我也。
贝多芬小时候因家境贫寒买不起乐器,便自制一些简单粗糙的替代品,并喜欢模仿各种鸟儿的叫声;达尔文从小对昆虫特别感兴趣,他经常捕捉各类昆虫制作标本,黙默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小时候常常偷看社戏的行为,使得他更早了解乡村生活的淳朴与童年友谊的真挚。特别有趣的是,他与小伙伴们偷摘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被六一公公发现后并未受到责罚,反而因豆子品质优良而感激他们识货。
说到底似乎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古今中外好多名人,他们小时候也是凡人,也有童伴童心甚至童闹,当然也做过许多“俗事”。
奈何我们一些普通人,反而容易把世上所有事物划分三六九等。没事瞎操心,人为地界定这高那低,主观地确认彼雅此俗,搞得人人自危无所适从。
这便是时人常常困惑不解的,为什么成年人的快乐没有小时候的纯粹彻底,没有曾经的天真浪漫,一句话,仰得太高了,想得太远了,要得太多了。得失之间,常令我们感慨良多,有时候在想,要是不长大该有多好呀!
可能正是因为自己自小笨、从来俗,我的一些“土办法”反而让我受益良多。我写《荷之物语》时曾到荷池“蹲点”一个礼拜,不管天热日晒,刮风下雨;写《竹节》时车子行至半山坡,望见山那边有片竹林,便停下前往观察体味,直到傍晚才回家;而写《读砚》时,面对憨态十足的砚台,我独自一人在书房把玩良久,陷入沉思……
直到现在,有好心人依然说我冷清刻板、中规中矩,示我不妨灵活变通以求跃升更高层次,可我自我感觉良好,尽管我行我素。
既然从小孤僻贯了,一直不适于“沙龙雅集”之类的群体活动,以至现在年纪大了还是“初心”难改。我仍是乐于三餐温饱喝点小酒,居家小院早睡早起。

(图源:CFP)
不知怎的,我一直喜欢每天清晨呆在自家楼顶的小菜园里,仰天上云卷云舒,望远处群山如黛,观蜂儿穿梭蝶儿翻飞。还喜欢看韭菜疯长,看茄子挂满枝头,看老伴种的苦瓜、丝瓜和黄瓜,欣赏它们长须缱绻的美……
如此俗吗?倘若说俗,但愿俗得真诚,也俗得可爱!
来源:泉州通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