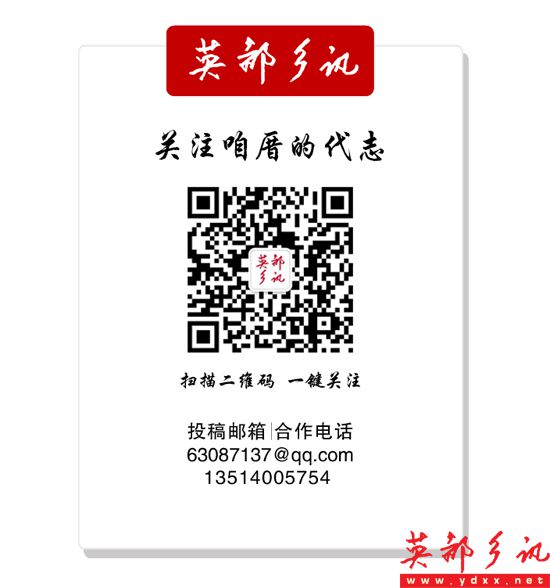作者:洪天平
书籍与石头,看似毫无直接关联,实则不然。它们之间始终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一种既神秘又质朴的联系。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尽管不少人常常忽略它的作用,但“怀才如怀孕”,日久自显,沉淀终会绽放光芒。
凡石头皆具神秘色彩,若非专业检测,俗人难知其来处。它们有的历经风雨侵蚀与地质变迁方才成形,恰如曹雪芹的咏石诗:“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
从现有认知看,石头当然比书籍亘古久远。某种意义上,石头是书籍的垫脚石,书籍则是站在石头之上的思想载体,堪称“巨人肩上的巨人”。
不知该上溯至远古何时,在时空隧道的某端,书籍与石头不期而遇,从此结下不解之缘,结伴而行。
憨厚的石头向书籍袒露心扉:自己经大自然的火山之手,将地层岩浆或点缀于山,或沉潜于海。于是,既有“石蕴山辉”的传奇,也有“海枯石烂”的美誉。
睿智的书籍向石头敞开胸怀:古代传说中,文字始祖仓颉,生就双瞳四眼,天赐睿德,察星宿、观鸟兽,循万象之形,终于革除结绳记事之陋,奠定方块文字之基。
一块石头,或大或小,或方或圆,小作摆件把玩,大可镇宅。常人视其不起眼,石却实心实意、宠辱不惊。岂知其上每一弯纹理、每一汪色泽,或藏着千年一瞬的故事,或沉淀着万古风化的沧桑。
当然,石头应感谢文字与书籍,若无文字书籍的传播,有口难辩的石头,不知还要缄默多少光年。
石虽不能言,却自有灵韵。少了文化的修饰,世人只能猎奇其皮囊之美,无法探究其包浆之厚重。
世间有一种缘分叫水到渠成。谁承想,不争不语的憨石,竟与字斟句酌的文学符号结为姻亲?或许是山土的融合之力、水柔的造化之功,成就了石头的恒心;或许是汉字的架构之美、象形之妙,俘获了世人的芳心。此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自书石结缘,彼此便互递纽带、共传心意,以石为基、以书为桥,不离不弃、相互借鉴。它们双向奔赴,沉浸式的交流令人赞叹,书因石而内敛博雅,石因书而风情万种。
寻常可见,书与石的交往从未大起大落,始终恒温前行。若说得文艺些,这叫“自带风骨,不事张扬”,因它们自然坦诚、从不矫情。古老的石头负责铺陈、造景、遣兴,直至沉淀为岁月的注脚;知性的书籍承揽诗意、禅心、想象,直至抵达梦的远方。
它们的协作源于默契,默契源于彼此欣赏。石头深知书的一端通向知识的海洋,书籍懂得石头是智慧的坚实阶梯,恰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高手切磋,无需赘言。大气磅礴的石头,以“石上凿字”的千钧之势、一诺千金的沉稳,博得书籍的青睐;明史达理的书籍,以才高八斗的风度,赢得石头的首肯。
赏石之人偶有发现:一块石头摔成两半,里边竟藏有硬核,这恰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异曲同工。
似我等俗人,亦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懂读书可滋心养性、拓展格局。平日里,我喜将心仪之石置于书房,让这两位智者跨越时空对话。最美不过书香气,在书山学海中,吾乃 “投石问路”之人。
书石合璧,亦庄亦谐;文武同框,一张一弛。耳濡目染间,或有所获。正如曹雪芹咏石诗所云:“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

注:原文发表于6月17日《泉州晚报》第14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