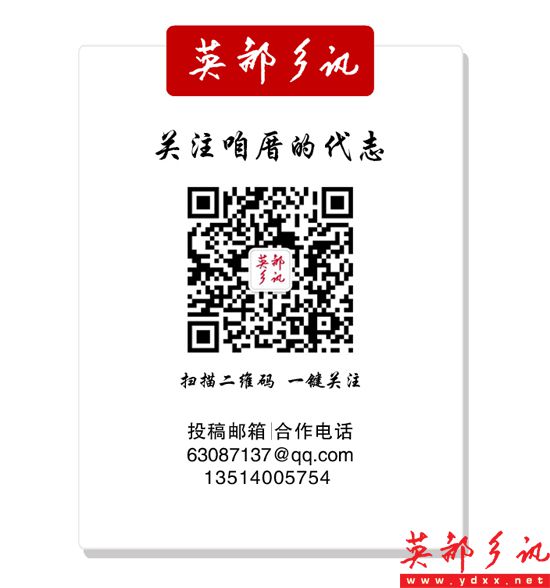吾家祖厝门口,有古井焉,位处原祖厝下落左角埕边,乃祖厝固有之配套设施。昔时闽南之地,凡完整大厝皆有水井相佐,以满足家族成员日常生活之需。其与祖厝同兴于清末,栉风沐雨近二百年,静立如初,犹若一部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去品味的古籍。因新村改造,井台随周围地势而抬高近一米,虽原貌有变,但其庄严神圣丝毫不减。宛如一位慈祥老人,见证了社会变迁、家族发展;记载了岁月沧桑;诉说着一段古老而又悠远的故事。

古井泉源丰沛,深不足六米,直径一米左右,高出埕面三十公分的圆型井盘约有三米直径,以石块和混凝土砌就,井壁鹅卵石垒筑而成,苔痕斑驳,良工巧匠尽蕴其间。每至晨曦乍露,取水之人纷至沓来,桶落泉涌,清冽之音,似初奏琴声,悦耳悠扬,弹响晨之序曲。水桶既出,水珠如帘纷落,于晨光中闪烁,若碎玉跳珠。此时井边的洗涤水声、水桶碰击声、互相道安问候声、连绵不断的呢喃笑语声和清脆动听的鸟鸣声共同编织成美妙悦耳的自然交响乐,这曲交响乐像一把美妙的音乐钥匙,打破了黎明的宁静,开启了一天的喜悦之门,令人心旷神怡。
往昔岁月,此井为家族之生命源泉。炊饮濯浣,皆赖于此。炎炎夏日,井水清凉宜人,捧之入口,清爽甘甜,沁人心脾,周边难觅。尚记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喜茗老干部下放到我村,住在我家厝边,常使唤我为他提水煮沸沏茶,据说所出茶汤罕见之甘润醇厚。若取之沐浴,更是暑气顿消。犹忆盛年之时,酷暑夏夜,汲水数桶,自顶浇落,凉意四溢,畅爽难喻,竟至乐此不疲。五叔爷每见,常诫吾曰“立秋之后,勿可冲凉”。冬日凛冽,井水温和,井面热气氤氲,水汽袅袅,如轻纱飘舞。于井边浣衣洗菜,寒意亦解。其景恰似精彩绝伦的乡村舞会,为传统的田园生活增添一道温馨而亮丽的风景线。

曾记儿时,每临井边,总俯身探视,水面倒映苍穹,人影绰绰,深邃幽蓝,神秘莫测,似有无尽奥秘深藏其中。尤其盛夏午后,日光正照,井底明晰可见,井壁卵石缝间青苔附生,水面部分偶有小草摇曳,似井之精灵,与水相依,共守岁月静谧。间或见井底有“鮕鮘鱼”游弋,闻说乃为防投毒而蓄养。
风雨如晦,朝代更迭,井独守一隅,无喜无忧。值社会动荡、战火纷飞之秋,井为村民庇佑,予生命之水,助众度厄。灾荒之年,旱魃肆虐,大地干涸,唯井水不竭,虽浅仍盈,取水灌田,抗旱保收,养一方生灵。井就是如此默默地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息繁衍,孕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未来,凝聚着所有家族乡亲的感情与记忆,其功青史永铭。
然世易时移,自来水入户,井已少用,现以不锈钢格栅蔽之,以防坠物。虽显冷落,然其于家族心中,尊崇敬仰依旧。游子归乡,必至井旁,轻抚井栏,感慨万千,倘以井为镜照心,则可映照出人之根本与初心。井也,非独生命之源,亦为宗族之根,乡愁之所寄。先辈远渡南洋,未忘家有古井,无论离乡多远,不管多久,见井如晤亲人,知祖之所在,遂觉心安。今之古井,虽已少用,然其文化符记,已深镌于家族传承之中。为老者谈资,孩童奇趣,代代相继,永不磨灭。
嗟夫!井者,水静而流深,清澈且甘甜,纳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容岁月之沧桑。蕴含着先祖的勤劳与智慧,展现了先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期望,其德厚流光,默默施惠,而不求闻达。以方寸之水,映乾坤之大;凭百年之寿,证尘世之变。家族因井而盛,家风因井而传。那源源不断的井水,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让我们铭记历史,心怀感恩,饮水思源,不负先祖的期许和勤劳,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砥砺前行,将家族的荣耀、先祖的精神和民族的文化永远延续。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古井都将继续守护着宗族人的心灵,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永恒的记忆。为家族精神之源泉,流淌不息,福泽后昆,留祉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