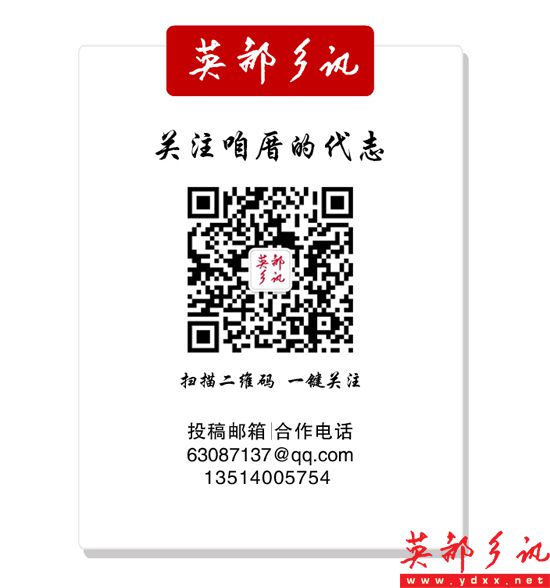1919年9月,我出生在南安英都石山村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每天辛苦劳作,只能让一家人勉强糊口。小时候的我,贪玩得很,像村里其他孩子一样,整日在山野间放牛嬉戏。不过,父母还是想尽一切可能,送我去上了几年私塾。我学了些简单的字,背了几句诗词,虽然不多,但也算是开启了我的求知之路。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当国民党部队的征兵任务来到家里时,我的父母皆已离世,长兄远赴南洋,音信渐稀。二哥成婚不久,膝下有了幼子,一家人虽日子清苦,却也守着微薄的温暖。征兵那时,刚成年的我,身形瘦小如柴,实在不符合入伍标准,将我拒之门外。决心从军的我开始软磨硬泡,终于,我的坚持打动了征兵官,我踏上了那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征兵路途,只为给身后的家人、给满目疮痍的祖国,拼出一片安宁。当兵两年多,我在南安当过民兵,到同安大嶝当过海防兵,后来跟随部队也到过福州南平建瓯等地方,最终因生病,面黄肌瘦,身体条件太差,实在跟不上部队的行程,经长官特批,带着一小袋米,就从建瓯县独自徒步500多公里回家了。
解放前的各种混乱,日子变得动荡不安。为了逃避被抓壮丁,我隐姓埋名,一路奔波到长泰厦门各地,到处给人家打长工。又听说我二哥携妻带子背井离乡也逃来同安县东埔,不久经山边(今东孚街道山边社区)堂姐洪晟她牵线,兄弟得以秘密相认(生怕同安当局知晓他俩是南安县来的亲兄弟关系),当时看见二哥一家东躲西藏,小家庭也特别困难,提议去“卖兵”加以资助,但兄及嫂坚决不同意,就没“卖成啦”。
解放前不久,我来到东孚过坂村当长工,遇到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苏钱。她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黯淡的生活。她温柔善良,眉眼间尽是柔和,我们慢慢相识相知,两颗心越靠越近,很快便结了婚、安了家。婚后,日子虽清苦,却满是盼头,我们先后迎来了3个儿子和2个女儿。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我没日没夜地干农活做木工,风吹日晒,手上满是老茧。苏钱也丝毫不轻松,家里家外一把手,操持着大大小小的事务,从洗衣做饭到缝补浆洗养家禽,事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那时候,我们一家老小挤在3间破旧的老房子里,空间狭窄,可经老伴的巧手收拾,总是干净整洁,透着家的温馨。
那些年,吃的是柴火饭,烧火时的烟熏火燎成了日常,可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我们相互扶持,不管生活多艰难,彼此的心始终紧紧相连,这份温暖,一直支撑着我们走过无数个春秋。
2015年,我和苏钱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金婚证,在过坂社区,我们也算是一对模范夫妻了。只可惜2024年5月,老伴还是离开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她留给我的回忆,足够我用余生去回味。

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号召参军,我毫不犹豫地让大儿子洪亚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曾在南海舰队服役,保家卫国。后来,我又让大孙子洪建设参军,曾在边疆去守卫祖国。看到儿孙们为国家贡献力量,我这心里满是骄傲。令人欣慰的是,曾孙洪冠诚凭借优异的成绩,保送进了985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24年8月,我听闻家乡树墘祖厝正在重建,心里满是感慨。祖厝对我来说,那是根,是对家族深深的眷恋与敬意。于是,我和家人为树墘祖厝的重建捐了一些微薄小钱。2025年2月9日(即乙巳年正月十二),应有福会长和理事会的热情邀请,我和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参加树墘祖厝重建落成庆典,并授予我名誉会长的称号,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一份厚重的责任。

回首我的这一生,岁月在我脸上刻下深深浅浅的皱纹,有过苦难,有过欢笑,有过遗憾,更多的却是满足。我从一个小山村的孩子,到如今儿孙满堂,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亲历家族在风雨中飘摇,又在和暖日光下重焕生机。曾历经缺衣少食的困窘,也感受过邻里互助的温情;品尝过背井离乡的苦涩,也收获了家庭美满的甜蜜。如今,我站在人生的暮年,过往的一切都已沉淀为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无论平坦还是崎岖,都被岁月赋予了独特的意义,成为我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
(洪天助之孙洪有志记录、整理于202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