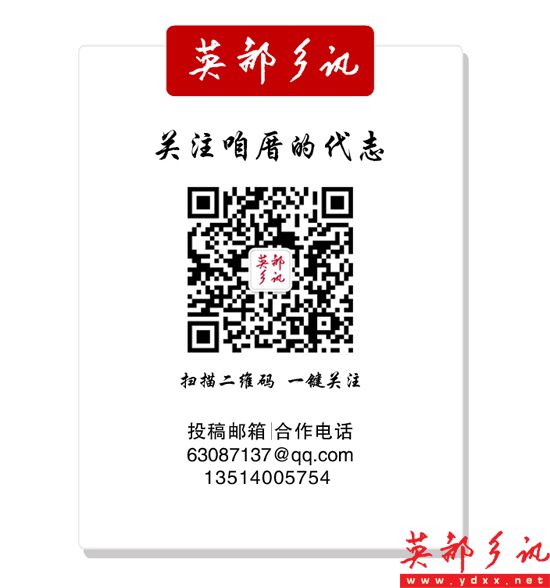作者:洪天平
紫山,又称狮子山,位于这个小镇的东边。紫山群峰巍峨,雄浑而大气,登临它的峰顶,能一眼望见泉州的双乳山。在紫山逶迤的山脉怀怉里,藏有“狮子岩”、“古竹岩”和“牛尾塔”,佛道同兴,岩寺并尊,实属罕见。
紫山脚下,有一弯汩汩溪流,曲折迂回向东而去。很久的遥远,多情而灵性的溪水,在此舒缓小憩,遂成就一汪长潭,“长潭溪”因此而得名。自唐至宋,此地便为英山商埠,码头风樯摇动,溪滨商铺林立。农业社时代,社员们常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挖到古时的坅石和砖瓦,甚至还有不少青石雕就的珠斗和拱梁,据此可以说“长潭码头”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之内河驿运的发祥地无疑......
十几年前,就在长潭古地,就在小溪两岸,勤劳智慧的村民再度演绎沧海桑田的传奇故事,续写商贾繁荣的不杇篇章。喜见各路英豪汇聚于斯,共襄古老码头的复兴之举,一个占地2000多亩的工业园区拔地而起。今天再登紫峰回望山下盆地,仿佛看到天方夜谭,其骤变的速度和规模让人有点不敢相信,就如梦里一般。当然作为乡人工业梦的孵化基地,发展需要科学次第,不可能今日播种明日催粮。

可以想见,昔日我们的丝绸、粮油、茶业、薪炭就是在此运往丰州泉郡,远航异国番邦。就在几年前,原地重建的那座崇祀海神的昭惠庙,无声有字地向虔诚的来客细述着这里的非凡过往。古地重光,并非简单的崛起和纯粹的复活,而是神韵的升华和格局的超越。拦溪为湖好荡舟,地上车道任纵横,多维的画面已是今非昔比。
如今那溪还叫“长潭溪”。有诗云:“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而我说:“古人不见此时溪,此溪曾经渡古人”,虽不尽合拍押韵,但意思已经到达。而于“长潭溪”的环弯回旋处,赫然闪出几座现代桥梁,记得造桥时上方征求桥名,我的意见得到认可,我认为桥的名字应该具备实地印记,还要有乡愁和古迹的韵味,就用周边的村落命名为佳。
是的,就叫“分水桥”、“后井桥”和“西庄桥”,“长潭溪”上横跨三桥,蔚为壮观。我以为,这是对古人的庄重慰藉,也是对古老码头的魂之再现和延伸。而今的长潭两岸,既有工业化现代化的大数据网格,又不乏小桥流水人家的古风辙印,古今同框,实属难得。谁言今不容古,和谐相安岂不最好。
“长潭溪”的拥弯地带,一个新兴的“白玉新村”悄然登场。为何唤其白玉,缘紫山脚下的这片丘陵古称“白石仑”,石即为玉,玉蕴山辉,故而得名。此并非杜撰,如今坡上还卧有一方巨大的原始白石,石身白得耀眼,它的身上藏着许多传奇色彩和神话故事。新村依山傍水,以轻盈灵巧的身姿立于林荫环抱的东临之阶,每天以“心略大于宇宙”的洒脱和无羁,看云卷云舒潮起潮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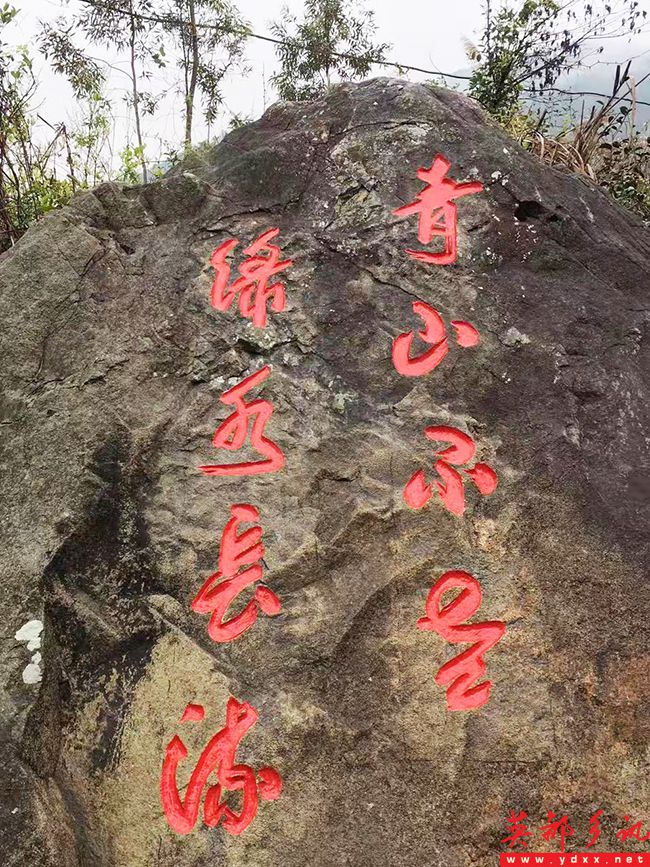
是的,新村的西隅便是长潭,潭水也有潮起潮落。为了营造氛围和主题,为了烘托古码头的历史元素,于“长潭溪”的下游又再造一桥一坝,皆以“白玉”赋名。桥过人,坝蓄水,于是自成一湖,又于是以“玉”命名。而今“玉湖”已现雏形,不言其大也不言其小,湖边有踏阶有卧石有芳草,湖中能泛舟能垂钓能幽会,玉石争辉,湖潭叠影,实在不可谓不浪漫。
漫步长潭两岸,当你踏上“后井桥”,接着再过“分水桥”,而后又去“西庄桥”,最后来到湖边的“白玉桥”。桥上的人们观“玉湖”风光旖旎,湖中的人儿仰桥上车来人往,熙熙攘攘。还有那“白玉坝”一帘弧形白水常挂,更添几分悠悠然神秘色彩。每当这个时候,常见走累了的人群,三三两两,自觉或不自觉聚到“白玉桥”东西两头的两棵大榕树下,指点湖水,谈天话地。二榕既与新村同时入驻,也见证“长潭溪”的再度“水暖”,如今榕的胸径要两人牵手方能合抱,榕树的枝叶伸到桥头探入湖中,一派园林景像。桥的东头立有一巨大石碑“玉湖记”,为人们提供傍侧注解,博得大家说好。

值得一说的是。几年以前,大约那个冬季刚过不久,在长潭溪的北岸,应许多熟人还有许多生人的要求,沿溪滨种了一排樱花,长长的,足有百来株之多,堪称樱花长廊。小小的樱苗落地后迎风见长,一季抽高一节,一年变苗为树,几年下来茎已碗口之粗。记得当时是请的台湾园艺师傅携苗前往裁种,樱花入驻,别具一格别样风彩。
游人觉得观樱花风姿、赏樱花芬芳有点异国风情,当然甚好。其实樱花并非舶来之花,据载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在中国宫苑内栽培,唐朝时则普遍出现于百姓私家庭院,当时万国来朝,日本国朝拜者将樱花带回了东瀛,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唐.白居易有诗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掘山樱满院栽......”以及“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后来樱花成了日本的国花,人家既然喜欢,那我们就慷慨与之分享吧。而且我还觉得,在古老的“长潭码头”种植樱花有其特殊的意义。既然自唐迄宋我们的诸多货物可以由此起航,远赴丝绸之路广交异国友邻,今日我们也该让这远嫁他乡的樱花回娘家欢聚。

有意思的是,长潭溪畔的樱花开得比别处晚,一般慢一个月还多。也许这里的樱花是想让世上拥挤的花海先行一步,自己作为后续花期,借以填补虔诚的花痴们到时失落的心绪。所不同的是,别处的樱花多植于坡上或园里,唯见这里的樱花长于溪畔之上。而正是此处独有的习习溪风和款款雨雾把多情的樱花滋润得别样妩媚,特别当少男靓女们走近那枝旁花间,看溪水倒映的人影和花容,始知原来自己与花儿竟是一样的美。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世事变迁,皆有轮回。冥冥之中,恍如穿越古今,如今的长潭溪滨已然化阡陌为商居,变小径为通途。嘈杂与恬静共存,混沌与清澈并驾,繁荣与幽闲不悖,如此才是多元的和谐,如此才是真实的“码头”。只要长潭水长流,美丽的“玉湖”便不会干涸。待来日,榕树更绿,樱花更艳,老醋新酿的“长潭码头”,将更加韵味无穷也。
老码头是首无字的诗。作为老码头复兴的参与者和旁观者,荣幸之余写下以上文字,聊作纪念。(配图洪天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