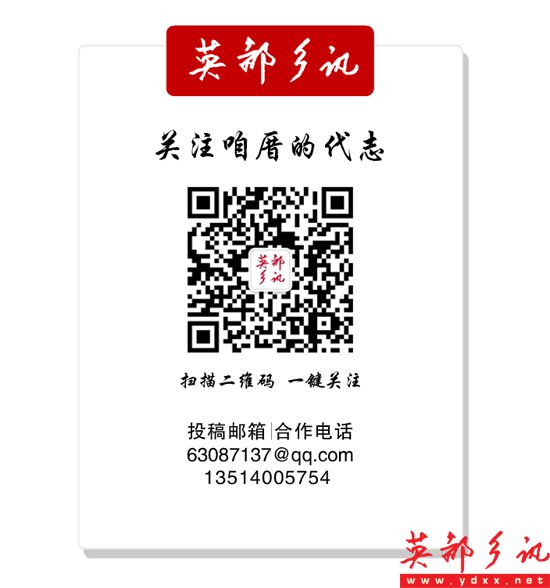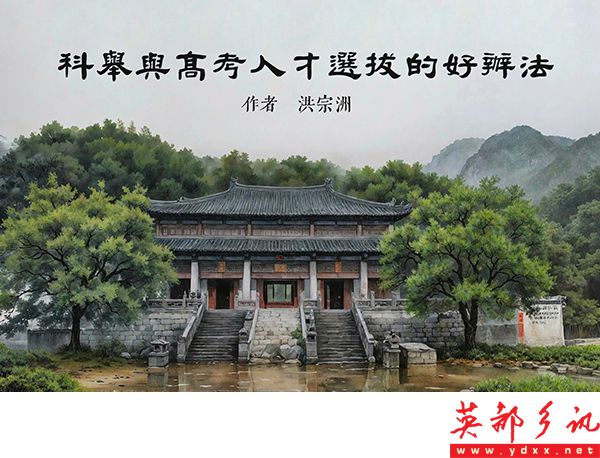
从踏入幼儿园开启三年启蒙,到六年小学夯实基础、六年中学淬炼思维,最终奔赴高考考场,现代学子需跨越十五载求学时光。这与古人“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求学历程遥相呼应,却在知识体系与选拔逻辑上展现出时代性分野。古往今来,教育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一代代莘莘学子奋力拼搏,孜孜以求于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谱写有为人生华章。
科举时代,士人以四书五经为圭臬,于《论语》“学而时习之”中领悟治学真谛,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里涵养家国担当;兼修六艺,在《礼记》“乐者,天地之和”的琴韵中陶冶性情,于《孙子兵法》的纵横捭阖间参悟谋略。反观当代高考,数理化构筑科学思维,政史地培育人文素养,分科体系深度契合工业文明与信息时代的专业需求。然而,日益白热化的“内卷”现象,也成为现代教育生态的特殊注脚——它既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折射出教育功利化倾向带来的隐忧。
当下高考竞争已呈白热化态势。家长为子女遍寻名师,从幼儿园阶段的启蒙课程到中学时期的奥数特训、作文工坊,从国际语言到前沿编程,孩子的日程表被切割成精密的时间碎片。学子们如韩愈笔下“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题海战术中日夜鏖战。标准化的“衡水体”书写训练、流水线式的应试技巧速成,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考试效率,却也让教育陷入“以物易性”的困境,背离了“立德树人”的本质追求。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如何在追求分数与培养人格之间找到平衡?
回望科举制度,其阶梯式选拔之路荆棘丛生。童生需连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方能摘得“秀才”头衔,虽获“功名初阶”,却仅取得参加乡试的入场券;三年一度的乡试放榜,中者得称“举人”,不仅获得仕进资格,更因“范进中举”般的戏剧性场景,成为科举文化的鲜活注脚。而“举人”之上,能跻身京城贡院参加会试者,已是各省精选的“贡生”,若能在殿试中脱颖而出,方能荣膺“进士”称号。这一群体不仅要经历贡院九日七夜的严酷考验,更需直面皇帝亲策。明代《万历野获编》记载,考生蜷缩于逼仄号舍,“三场辛苦磨成鬼”的诗句道尽科考艰辛。明代初期,朝廷默许考生于秦淮河畔雅集消遣,《板桥杂记》中“灯船毕集,火龙蜿蜒”的盛景,恰折射出科举制度背后复杂的文化生态——它既是严肃的人才选拔,也催生了独特的休闲文化与社交网络。
将清华北大录取与古代进士及第简单类比,实为认知误区。当代顶尖学府培养的专业人才,虽在现代学科领域造诣精深,但其知识架构多聚焦理工或人文某一维度。反观古代进士,需通经史、晓治乱,既能引经据典撰写治国策论,又能以《资治通鉴》为镜剖析时政,其学养的广博与思辨的深邃,远超现代单一学科培养的学术精英。此外,科举三年大比取士三百,年均仅百人,各省配额寥寥,稀缺程度堪比当代两院院士。但二者的差异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时代赋予的使命:古代进士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维系传统社会运转;现代精英则以科学技术为武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二者虽处不同时代,却同为国之栋梁。
福建南安市英都镇的翁山洪氏家族,堪称科举文明的活态标本。自宋末元初肇基,“诗书传家远,耕读继世长”的祖训代代相传,纵使早期四代单传,仍未改耕读传家之志。至明清时期,人口不足三千的家族迎来鼎盛:18位进士蟾宫折桂,洪启睿高中万历壬辰科会元,殿试传胪,其清廉风范载入《廉吏传》;65位举人、63位贡生、570位秀才如星河璀璨。“祖孙四代十进士,父子一博双翰林”的佳话,与《三字经》中“窦燕山,教五子”的典故交相辉映。明代洪启初、洪启胤堂兄弟官至左布政使。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家族对教育的重视,更印证了科举制度对地方文化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翁山洪氏族人的洪承畴,于万历四十四年高中进士,历经明清两朝宦海沉浮,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顺治年间,他以主考官身份参与科举,凭借深厚的经史功底与政治阅历,为清廷选拔治国人才。而清代洪世泽以“天下三博”之誉入翰林修史,老翰林洪科捷效仿陶潜,投身书院传道授业,延续文脉薪火。如今二十余万翁山洪氏后裔在政、农、商、文各界各展所长,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实践。这个家族的故事,正是科举文化从历史走向现代的生动缩影。
当科举与高考在文明长河中相遇,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就此展开。科举承载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追求,以经史礼乐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塑造了士大夫“为天地立心”的精神品格;现代高考脱胎于工业革命后的教育范式,以科学知识为基石,肩负着培养时代建设者的使命。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如黄河与长江并行不悖:前者流淌着文明基因,后者奔涌着创新动能。唯有在古今交融中汲取智慧,让人文情怀与科技力量共生共荣,方能培育出既深植文化根脉、又具全球视野的时代新人,续写人才选拔的千年华章。
(写于2025年6月23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