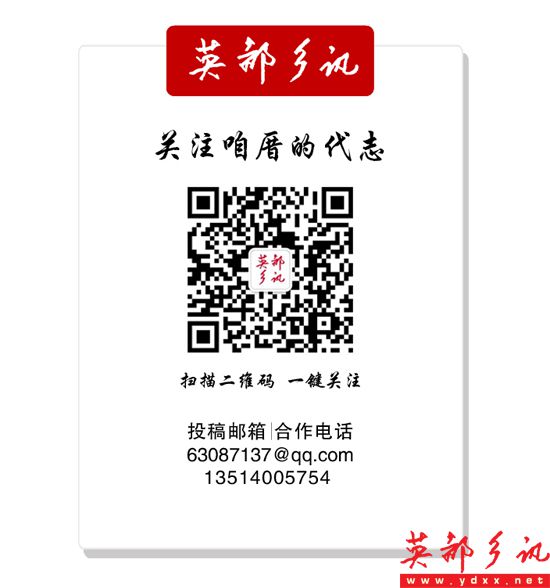人物:洪世泽
洪世泽(公元1708年—1791年),字叔时,号艮堂,南安英都人。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七月,以廪生身份赴京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经乾隆殿试毕,钦定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回乡后,相继受聘福州鳌峰书院、厦门玉屏书院、南安丰州书院任山长。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斐亭诗文集》《易经观象》等书。
遗迹:待驾桥旧址
待驾桥旧址位于南安市英都镇民山村,乾隆皇帝多次下诏,催促洪世泽回京候旨的接诏之处。待驾桥如今已被水泥覆盖,从边缘处依稀可见当年古桥痕迹。桥头有棵枝繁叶茂的榕树,三四百米处,曾有洪世泽回乡所建府第“少翰林衙”。

父子入翰林 辞官兴书院
苏清彬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性格、心思让人捉摸不透,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历朝历代的朝廷重臣,常因君臣关系处理不好,落得朝不保夕、身败名裂,甚至横死刑场。
二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跻身朝堂,是学会左右逢迎博皇帝欢心,还是敬而远之退避山林?南安英都的洪世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远离君王,成为家乡一代名儒。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天下有三博,英都得一博”的说法。这一“博”指的就是洪世泽。
时间上溯200多年,出生在乡村的洪世泽博学多才,在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中脱颖而出,深得皇帝喜爱,被安排到翰林院任职。尽管圣眷正荣,但他很快厌倦每日如履薄冰压力山大的生活,年纪轻轻便选择“激流勇退”。尽管乾隆皇帝多次下诏催他回京复职,但都被他以眼疾为由推辞。
寻待驾桥
再次造访历史名镇英都,已是仲秋时节。知道来意后,当地热心老人说要带我们先到一个神秘的地方走一遭。
沿着英溪岸边行走,两岸楼房林立、绿树成荫,乡村美景尽收眼底。走到民山村尽头,一座破败的房子呈现眼前,房前有一座窄窄的水泥桥。桥头一棵榕树矗立,盘根错节,枝繁叶茂,静静地守候着什么。

▲当年洪世泽就是在这座小桥前接圣旨
再往前,随处可见的青石板被磨得发亮。若非老人介绍,很难想象,脚下这座看似平淡无奇的小桥,便是当年乾隆皇帝多次下诏,催促洪世泽回京候旨的接诏之处——待驾桥。待驾桥现已被水泥覆盖,从边缘处依稀可见当年古桥痕迹。
古时英都通往泉州以及更远的地方,除了陆运之外,还有船运。而以前泉州到往英都的船运停靠点之一,就是现在的英溪董林桥。船只停靠后,最先进入待驾桥。洪世泽回乡所建府第“少翰林衙”,距待驾桥仅三四百米。
桥下流水淙淙,时光穿梭。这座待驾桥,目睹了从京城发来的圣旨抵达英都行船靠岸后,洪世泽多次跪地接旨的场景。
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洪世泽的祖父母相继去世,世泽遂上表陈情,归里殡祭,从此不再担任京官。惜才的乾隆皇帝多次下诏,希望他能继续效力朝廷。但他内心已有笃定前行的方向,均以眼疾委婉推辞。
待驾桥仍在,“少翰林衙”府第却早已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其父洪科捷位于英东村白灰厝后的“老翰林衙”也已圮废。
父子翰林
提及洪科捷、洪世泽这对“父子翰林”,英都从事地方历史研究的廖榕光最有发言权。洪科捷25岁中举,53岁中进士,以才优选入翰林院。洪世泽中进士比父亲早两年,授“翰林院检讨”一职。
这位被乾隆皇帝赏识的南安人,之所以走上仕途,受父亲影响颇深。年幼时,洪世泽显得比同龄人成熟,“静重如成人”。年纪稍长,经常从父亲书架上取出藏书研读,读后放回原处,并把书籍叠放得整整齐齐。抱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心态,少年时期的洪世泽学业日渐精进,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以弱冠之年考取廪生。
在县学读书时,洪世泽作文优异,深得督学周力堂赞赏,称他是“异日著作手”。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朝复开“博学宏词科”,这是一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恩科,举荐各地鸿才硕学,不分已做官或未做官的,都定期到京,在殿廷举行考试。经由福建巡抚卢焯推荐,洪世泽赴京应试。彼时福建推荐10人,泉州占了6人。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三月,各省推迟引荐诸子50余人,补试于体仁阁,乾隆皇帝主持殿试。首场试策二篇,第二场试诗、赋、论各一篇。试毕,皇帝钦定江苏万松龄为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云南张汉、浙江朱荃、福建洪世泽三人并列为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俱赐进士出身。因洪世泽名列二等博学鸿词三人之列,故泉州一带有“天下有三博、英都得一博”的说法。
两年后,洪科捷亦进入翰林院。父子双翰林,这在古代泉州府尚属少见。英都人深以为豪,为了区分开来,称洪科捷为“老翰林”,洪世泽为“少翰林”。这段历史佳话被写进了洪氏家庙,“祖孙四代十进士名扬明室,父子一博双翰林誉满清廷。”家庙大厅中这副楹联后半句,述说父子俩曾经的荣耀。
而在洪氏家庙东轩,洪世泽所撰楹联“解元传胪鸿博第,将相公侯郡马家”,写尽家族荣耀,“鸿博”指的就是洪世泽。
两度归里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洪世泽晋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他的才学得以施展,曾作《圣祖躬耕耤田恭纪》诗三首,歌颂清廷重视农业生产,皇帝不失天时,亲耕农田的举措,将其统治喻为“舜日尧天”。
据传,乾隆帝十分赏识洪世泽的才华,常与他谈古论今,又经常拿一些莫名其妙的难题考他。有次,乾隆让洪世泽到后花园陪玩,说来也巧,刚好一群鸟从西北方向飞来,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时而快,时而慢。
乾隆指着天上飞过的小鸟问道:“这是什么鸟?”洪世泽说:“此鸟在臣的家乡叫‘七沉鸟’。”乾隆说:“既曰七沉鸟,为何刚才起飞顿了八次呢?”洪世泽回答:“本是七顿,他见了君王,自然要加一顿,方为大礼。”
又有一次,乾隆来到洪世泽的书房,他的手里抓着一只画眉鸟,问道:“卿可知朕要把这鸟掐死还是放生呢?”洪世泽回答:“且容臣退后两三步再答。”乾隆准奏。洪世泽就势退到门槛,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答道:“皇上安知臣此时是欲进耶?退耶?”
乾隆皇帝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赞:“爱卿才思敏捷,确实名不虚传啊!”虽然每次诘难都被洪世泽以睿智应付过去,但他总觉得伴君如伴虎。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春,洪科捷以“双亲年逾八十”为由携儿子一同“告假归养”。
洪世泽告假没多久,乾隆就一再下诏召回。因感戴皇恩,公元1740年冬天,洪世泽便带着弟弟洪世润进京,入职武英殿,担任国史馆校对,并纂修《八旗通志》。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春,洪世泽回乡殡祭祖父母后,以眼疾为由不再担任京官。

▲英都洪氏家庙,洪世泽留下的对联。
儒者家政
回到英都的洪世泽,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读书之余,亦喜吟咏。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升任福建巡抚的周力堂,深知世泽无意仕途、一心向学,于是力邀其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席,期望有功于福建教育事业。
洪世泽遵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先贤所制定的学规融会贯通,并将之引申发挥,讲明治学与修身等道理,令学生受益良多。执教期间,重振学风,造就了不少人才。4年后,又到厦门玉屏书院、南安丰州书院讲学著述。

▲丰州书院,洪世泽曾在此担任山长。
担任丰州书院山长期间,洪世泽特别注重开放式教育,亲自讲学,允许学子在课堂上与他展开学术争论,鼓励用学术的思维思考问题,培养学子的创新精神。这给当时泉南各地书院树立了典范,为时人所传颂,到如今依然还有其现实意义。
他还对历史建筑、名人遗迹、教育之风等方面多有贡献。世泽见南安孔庙殿庑、棂星门等建筑残损,就召集人员一起修葺;栖居英都时,建始祖祠,修学宫,希望族人“敦本尚实,返璞还淳”。晚年,为了表彰先贤不遗余力,“重新欧阳行周应魁亭,迁葬会元傅夏器墓”。
为八闽文化先驱欧阳詹重修的应魁亭,现已不见踪迹。不过从仅存的应魁井、慈济宫,仍可还原应魁亭当年的旧址。“武荣慈济宫”在丰州南门街,红砖古厝建筑在这条充满商业气息的街道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庙宇,原址位于丰州城内丰乐铺,明清以来历经迁址、重建。就在宫前所在位置,曾有座为纪念欧阳詹荣登进士而建的应魁亭,因此武荣慈济宫又称“应魁慈济宫”。如今,宫前空余戏台一座,对面的小巷子里,留有一口封存的应魁井。

▲丰州南门街慈济宫对面,是应魁亭的旧址。
洪世泽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斐亭诗文集》《易经观象》《诗经订序》《春秋订传》《周官析疑随笔》《仪礼辨说》等,惜大多散佚无考。
“居官当尽职报称,斯不负科名。若退而家居,上治祖宗,下治子侄,推而及邻里乡党,此儒者家政也。”父亲的谆谆教诲,或许改变了洪世泽的一生。(来源:海丝商报,图片由本报记者李想拍摄,感谢廖榕光先生对本次采访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