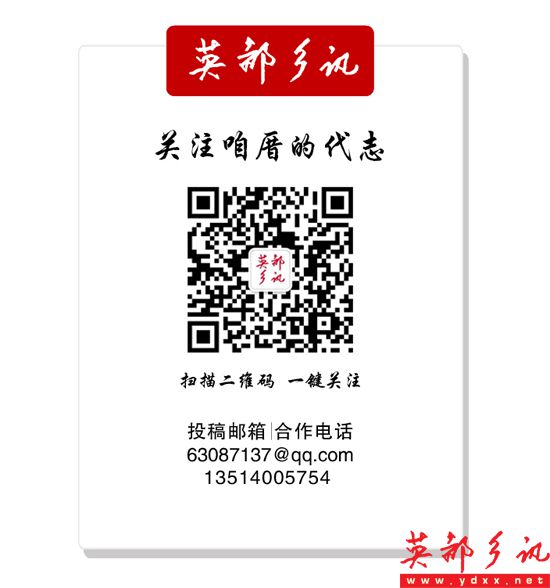作者:洪天平
古往今来,凡有人居的地方便有水井。如今这句话可否修正为凡有古厝人家便有水井。
“井”字象形,金文字形,外象井口。据说古时还在其中间加上一点,为“井”,喻井里有水。如今井字规范写法是两横一撇一竖,亦可泛化为两横两竖。四根棍子,横竖交叉,且无论从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观之皆为“井”,这是汉字的神奇更是“井”的魅力。依照井型框架,当初“井田制”可以向四方任意等量延伸以至无限,构成如现代的“网格化”管理,跨越千年竟有如此神似之处,真佩服古人的超凡智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此说来,古人凿井是为了农耕,或是耕饮并用。渐渐地,井的使命得到了进化和升华,在往后相当长的历史以至现代,井,井水,百姓之饮,生命之源一直是它的永恒主题。
寻常见,古厝屋角,一口古井端坐一隅,它是井邑的缩影,更是民生的基本保障。因为有了井,世间得以孕育多少后代儿女,使得万物生生不息,生命薪火不断,即所谓“暮犬晨鸡井不离”。于是乎,千百年来,井的传说,井的故事,史传书载,诗赋歌咏。如果说世上有哪一种事物能够获得只褒无贬洁净无瑕的殊荣美誉,我敢说只有井,唯井独尊也!井是“佛系”杰作,敛息屏气大音稀声,一生为水却从不追“潮”,实在难得。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口井,宽三五尺,深二三丈,口小腹大,直肠直肚,看似平庸无奇。尤其那敦厚的井座,憨如土地爷。就是它,扎根地之深处,日夜不息采集泉源汇聚成井,拱手奉给天下百姓,而且来者不拒童叟无欺,不分贫富无论官民,一样的笑脸相迎,一样的冬暖夏凉。井的出现,衍生了多少“井”的文化。井然有序,井井有条,它是规矩和纲常的代名词。“水不洗水,尘不染尘”,如若拟人化,井可以说是集绅士、善者、仁人、禅心于一炉的大爱化身——
井,矜持儒雅。井中之水没有激流,不见波澜,更无瀑布,人们很难于井沿之上听到地下泉眼的汩汩之涌。即使婶子姨娘打水时轻摇水桶留下的涟漪和叮咚也只在井中荡漾和回旋,而且转瞬复归平静。没有顾盼,从不乞怜,守拙本分是井的独家之道。
井,缄默无语。它自濯自洁自我沉淀,不满不溢也不冒泡,而且自设律架,井箍即是约束的尺度。关于乡野市井之风云,关于汉子村姑之秘事,它抱定只拿耳闻毋须置喙,或许是深藏井底了。即使粗犷的村夫在井台烙下无数绳痕,它也微笑接受。此等“身似菩提心似镜,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境界,人间少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井,不卑不亢。虽是“井底观天”,却深藏睿智,一井之水如同天文眼镜,洞穿穹宇。井当然熟谙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含意,更晓得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以及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情怀。而我又何德何能,大地竟然慷慨地赐予自己永不枯竭的源泉,我只有让甘醇清澈的一汪井水始终注满真情。
井,乡愁悠悠。自从认准了在乡间屋角蹲守,井便成为一方乡民的诚信依托。井常对大家说,如果生活需要离乡背井去打拼一番天下,你们无须牵挂,家里有我就不会断了炊烟。每见青山忆故居,归来时,我定在村口等你。如此“井臼亲操”怎么不让人动容,滴水之恩并非井之所欲,涌泉相报才是井的无悔选择。因为井是乡愁的符号,而且是嵌入地层深处的符号!
是夜,取自家古厝古井舀来的水煮茶。古厝和井是乾隆中叶的,近300年了,井水依然清冽甘甜。“古人已别此井,此井曾奉古人”。品茗望月,井思绵绵,聊作《井赋》,以表仰慕之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