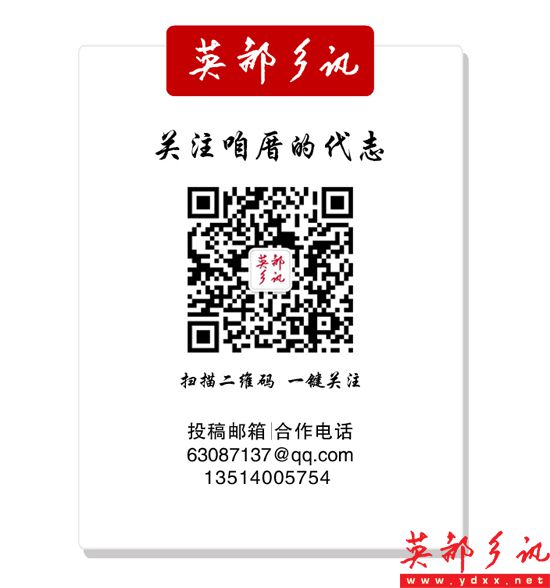作者:洪天平
打从记事起,五、六岁的我便有了憧憬,这应该不算早熟,大概凡人都是一样的。
那时候年纪虽小,但穿衣吃饭是人的天性。夜里常常梦见过年了穿新衣裳,还吃到一碗喷香的炖肉,再加两个鸡蛋;梦见在村道旁的水沟边捡到几枚硬币,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从此开始富有,可以买作业本子和铅笔,还可以买糖果,分给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对我可好了;梦见自己长高了,长得很高很高,伸手就能摸到天上的星星,在星空里自由地嬉戏……早晨醒来,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离过年时间还很长,还要一日一日地挨。肚子还是很饿,生活还是那么穷,穷到作业本子要两面写。个子也没长高多少,离星星还是那么遥远……美好的想像总在梦里出现,但醒来又要面对眼前的现实,又要脚踏实地过日子。身上的担子过重,稚嫩的脚步都有些踉跄了。“度日如年”这个成语,现在的孩子不懂,或者不甚懂,那时的孩子懂,甚懂。

(图片来源网络)
稍大点时,总喜欢家里有亲戚来或者可以出去走走亲戚。“来了”,款待亲戚时锅里幸许还能剩点,沾点油星子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去了”,便是改善伙食的绝好机会。记得有一回到了山外的亲戚家里,中午时候挨家到三兄弟那里串门,他们每家都煮出一碗点心,山里人虽穷但礼足,一碗上面还用另一个碗扣着,打开一看是上下两碗的咸肉炒米粉,第一家来者不拒,三下五除二就收拾碗筷了。第二家也是咸肉炒米粉,而且如法炮制,上下两层,难得如此厚待,还是撑下去吧,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第三家依然是咸肉炒米粉,为什么呢?山里生活紧巴,备点稀货是为招待客人的,只有咸的干的能久藏。三家三碗,其实是六碗,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行了,眼睛不饱肚子饱,随便扒拉两口就把筷子放下了,“好食不称饱人意”呀!但亲戚也不能每天走,否则就讨人嫌了,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还是家里的稀饭汤萝卜干管用。就像天上的星月很美很迷人,你可以停下脚步一阵仰望,但终归要低头走自己的路。欲望催人奋进,勤劳才有饭吃。仰望把握方向,低头迈稳脚步。
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是孩子们向往的日子,像盼星星和月亮一样,掰着手指倒计时数着它们的到来。因为初一和十五是传统“犒将”的日子,一般在傍晚时分,每家备一锅干饭和几个比平常好点的菜,没有肉也要滴点油。“一敬神二敬人”,在家门口点香焚金后,各自端回家里聚餐,孩子们庆幸终于可以吃到干的了,可以打打牙祭了。只是当遇上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即使初一、十五这样的日子也要打折扣了,记得有一次终于又等到初一了,下午放学我满心喜悦蹦着回家,当我到家打开锅盖一看,干饭还是干钣,但里边却放进了好多“地瓜签”,我顿时皱起眉头,又是地瓜饭,月月如此,日日如此,简直都“审美疲劳”了。当时想过——确实想过,将来若有出头的日子,一定先把这倒霉的番薯芋头枪毙了。后来我曾不只一次听伙伴们说,他们也发过默誓日后不吃番薯芋头。说来好笑,谁曾想现在的日子好了,大家还是怀念番薯芋头,油腻东西吃多了总想清清肠子,这大概也算是一种返璞归真吧。其实初一和十五,一个月里只有两天,但它却成了孩子们仰望的星空,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哪怕是瞬间的饱暖也是难得的。“两天”先过,二十八天在后,漫长的日子还要用瘦瘦的脚板一步一步丈量。年复一年,岁月更迭。读书很苦,家务很繁,农活很累,这一切都需要脚踏实地,负重前行。
只有夏天的夜晚,最是浪漫的时刻。读书时的伙伴聚在月光下的草垛上,望着天上灿烂的银河,开始议论懵懂的人生,也谈些严肃的理想。尽管眼下过着糠菜的日子,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是少了最要紧的钱票,然而这帮少年嘴里已然有了大人的语气,甚至诗人的口吻。“面包会有的”。“好男儿走四方”。“苟富贵,无相忘”。“天上的星星在看着我们,会护佑我们前行的”……许多年后,当彼此久别重逢时,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遗憾,有顺风顺水撑大船的骄傲,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长大了,成熟了。“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龙应台《目送》),是非成败早已经释然了。然而我总在想,人这一辈子要是没有理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理想有些卑微和短距,但终归是生命的动力,是心中的明灯。我还在想,人这一辈子要是没有务实,就像鸟儿没有窝巢,先把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耕种好了,就有温饱,就能赶路。

(图片来源网络)
星空赋予我们诗意的灵魂,又教给我们驾驭的才能。大地恩赐我们坚实的臂膀,又传授我们生存的智慧。我们也会陶醉琵琶古琴的悠扬,但更需要锅瓢盆的碰撞,我们也能欣赏秀竹幽兰的雅韵,但更渴望粗谷杂粮的充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便是我们成功渡向彼岸的双桨。